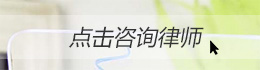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城镇国有土地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土地由既往的无偿、无期限、无流动的使用模式趋变为有偿、有限期、可流动的使用,土地资产价值已广为人们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市场价值愈加显现。土地的交易流转,是实现土地资产价值的重要途径。1990年代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刺激了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以让渡土地使用权获取收益的欲望。而鉴于政府征地补偿费与土地实际使用价值相差悬殊,农民并不希望集体拥有的土地被轻易征用而永久失去土地收益的所有权;在平等观念支配下,认为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不同的“出身”不应该影响各自主体权利的地位——如同国家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拥有完全的土地处置、收益等权能一样,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收益权也应完整地归属于集体土地所有者。
在经济起步早发展快的东部沿海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多年来蓬勃发展的制造业、商贸业与持续加快的城镇化,导致建设用地需求量急剧增长。而随着国家对土地供给宏观调控不断加强,城镇国有土地可供量已变得捉襟见肘。2003年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反映,山东已使用城市规划用地的80%,浙江超过90%,一些地区5年就超量用完10年的指标,如广东东莞当时在未来5年内只剩下6万多亩用地指标。在国有建设用地供给稀缺状态下,城市的再扩张和工业的持续发展使得盘活集体建设用地势在必行,这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了机会。只要得到市场需求的认可,集体建设用地也同样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资源要素进行流转[1].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数量约相当于城市建设用地的2.5倍,各为约1700万公顷和700万公顷。尽管集体建设用地一直游离于土地市场以外,国家立法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入市”存在种种限制,集体建设用地的资产属性与市场需求特征也日渐显露,以出让、转让、出租、作价(入股)投资等形式自发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现象早已存在,在数量上和规模化呈不断扩大趋势,演变为关系错综复杂而庞大的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这是不争的事实,珠三角地区尤为典型。该地区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大多是以土地经营为主,即以土地出租或在土地上建厂房或商铺出租等形式获得土地非农收益,既是农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农民最直接稳定、最为长久的收益保障。据统计,珠三角地区近些年通过自发流转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实际超过集体建设用地存量的50%,即使在粤东、粤西等地,这一比例也超过20%.
长期以来,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自发流转在客观上对农村社区经济发展、集体财富积累、社区管理服务及稳定农民收入等起到了保障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流转毕竟是在政策法律上未得到明确的认同,在杂乱无序或隐蔽状态下进行,缺乏合理的规制,从而难免地引发诸多问题,容易滋生不少土地纠纷及矛盾冲突,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其弊端主要表现为:
其一、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自发无序地流转,导致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被削弱,难以有效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冲击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有效实施,造成土地利用混乱,土地市场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其二、隐形市场活跃,违法用地屡禁不止,耕地保护受到冲击。受流转利益的驱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耕地保护的意识淡薄,不愿意承担耕地保护的义务。未经批准随意占用耕地并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建设,或低价出让、转让和出租农村集体土地,交易行为扭曲,工业用地以联营为名行转让、出租之实,住宅用地则借房屋出租或私自转让进行市场交易。
其三、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权利缺乏可靠保障,交易不安全。由于集体土地依法不允许出租,对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的条件、用途、权益等缺乏明确规定,难以依法进行土地登记;加之流转主体(主要是集体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流转程序失范,对建设投资者也不利,还会波及到其他利害关系人,交易安全得不到保障;权利设定缺乏合法依据,由此引致流转法律纠纷不断,一旦调处失当,极易酿成重大社会案件。
其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分配关系混乱。由于缺乏依法监管与市场机制,土地市场价值和资产资源属性在流转中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国家土地税费流失严重,加上农村土地产权关系混乱、集体经济组织结构不完善,使得本属于农民集体及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亦难以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
总之,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化、商品化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入市的理论依据,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导致对非农建设用地需求急剧增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发流转处于法律上的 “灰色”地带及伴存的种种问题,对获得相关法律政策支持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而,法律政策将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流转纳入调整范畴并合理规制是顺理成章已势在必行的。
阅读推荐:房屋买卖合同的违约策略及应对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