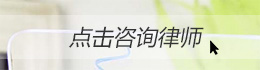在当前还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申诉听证制实际上是把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申诉作为了一种再审之“诉”来处理。其创造性、超前性和重大价值显而易见,所具有的内在合理性及实际产生的效果也得到了较普遍的承认和认可。它的理念和操作方式,同再审之诉模式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它把再审申请、申诉的审查作为了一种程序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准备阶段”来看待。“申诉复查程序是事实上的诉讼程序”,是“因谋求诉讼公正在实践中产生的诉讼程序”,“申诉复查程序的产生是审判监督程序的完善”。[8]其二,更为重要的,它通过“敞开大门”、“有诉必理”、“只要有人‘击鼓鸣冤’,法官必须‘升堂问案’”的来访申诉听证制(信访听证)确保了当事人的申诉、申请再审得到“诉”的回应,这与再审之诉模式开放式再审的精神完全一致。[9]其三,它明确了听证是再审申请、申诉审查的最理想方式。听证不同于开庭审理,但又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和直接性,较充分地体现了“审查”的特点。无疑,再审之诉模式下的“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也应当以听证为主要方式。
然而,申诉听证制毕竟受制于现有的立法框架。再审之诉模式得到立法支持后,其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将与现行的申诉复查听证制产生较明显的四点不同:
一是再审申请的受理、再审申请审查程序的启动将更体现开放性。“将不设置任何实质性条件”,只要求再审申请符合程序性要件。而现行的信访听证后的复查立案,仍对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一定审查,排除了“明显”不具有再审事由的情形。二是在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运作过程中,无论是其立案,还是审查结果的“驳回”,将一律采用具有明确法律效力的“裁定”,而不是现在的“通知”。由于具有了明确的法律效力,裁定的适用可能带来超出其结果本身的影响力,使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具有更大的价值。例如,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在阐述驳回理由时可能修改生效裁判的瑕疵或者是补充、完善生效裁判的说理使之更具合理性。按一般的法理,裁定的理由也应具有法律效力,由此,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尽管在结果上维持生效裁判,但实际已对生效裁判作出了“改判”,而这种“改判”可能使生效裁判更完善。这样,再审申请审查程序的价值将不仅仅只是对进入再审审理程序作出判断,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完善生效裁判的作用(当然也有可能是负面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司法裁判文书质量不高,当事人难以服判息诉的情况下,再审申请审查程序的这种作用可能显得格外有意义。三是申诉听证制下的两个“听证”即申诉人单方参加的信访听证、申诉双方参加的复查听证,将不作为两个阶段来严格划分,而呈现融合。信访听证的主要功能在复查立案,解决“申诉难”。在再审申请的审查程序下,这一功能可以通过再审审理立案来实现,而这一立案因不“设置任何实质审查条件”,因而可以不必采取听证形式。这样,信访听证、复查听证的区分可能变得意义不大。但是,在其后的实质性审查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形如是否驳回,区分申诉人单方参加的听证和申诉双方参加的听证可能仍具有重要意义。四是再审申请受理的程序性条件、再审事由的审查标准将更规范、更具体、更严格,更体现“限制”的特点。
阅读推荐:一起遗产继承纠纷中的法律认定